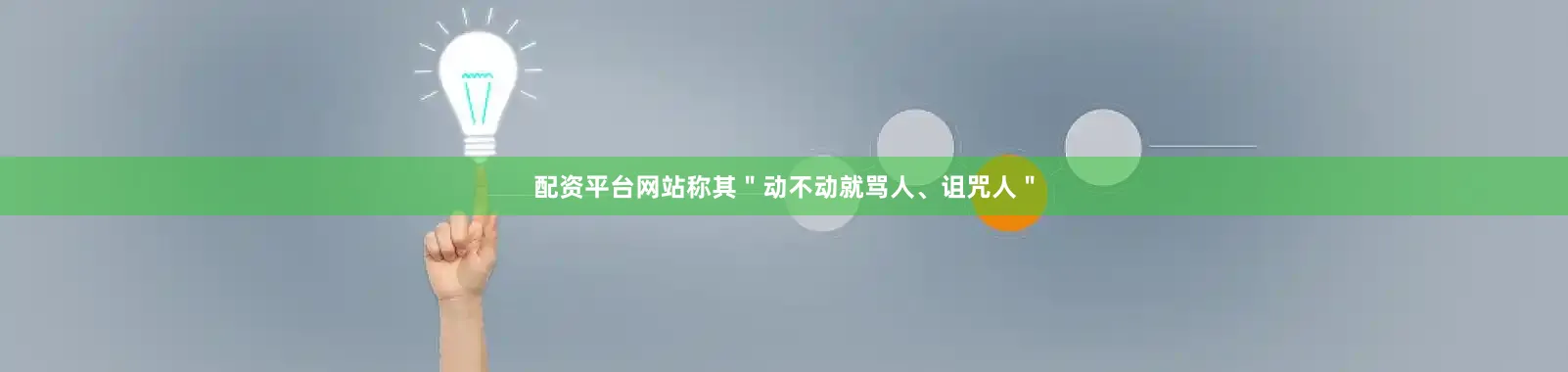菩萨蛮
2011/1/28(腊月25)
秋风百草凋零透,黄花翠竹皆清瘦。唯剩去年香,依然旖旎芳。 人间难再少,离别须臾到。仍执本心归,不劳霜雪催。
腊月二十五,年的气息已经开始在广西凤山的山村间弥漫,但罗红端的生命却走到了最后的冬天。这首《菩萨蛮》是她留在人间的最后一首诗,每一个字都像是从即将熄灭的生命烛火中提炼出的精华,凝聚着她对生命的最后思考,对美的最后追求,对命运的最后回应。这不仅仅是一首词,这是一个灵魂在离开人世前最后的自白,是她在生命终点完成的最后一部艺术作品,也是她留给这个世界最深情的告别。
“秋风百草凋零透”,起笔七个字,写尽了生命的荒寒。“透”字用得惊心动魄,不仅是草木凋零的表面景象,更是生命本质的彻底裸露。这个“透”字里,有她对病痛最深刻的体验——那种寒意不仅来自肌肤,更深入骨髓;有她对命运最清醒的认识——生命的凋零是不可逆转的自然规律;更有她对人生最透彻的领悟——所有表象终将褪去,唯有本质长存。可以想见,病榻上的她,感受着身体如秋草般一日日枯萎,在无数个疼痛难眠的夜晚,她反复咀嚼着生命的滋味,最终提炼出这个力透纸背的“透”字。这个字,与她在《巫山一段云·雪》中写的“冷暖不由人”形成深刻呼应,都是对生命本质的终极洞察,但此时的领悟更加深刻,更加决绝。
“黄花翠竹皆清瘦”,这句转折精妙非常。菊花本该在秋风中傲霜挺立,翠竹本该四季常青,但在她的眼中,连黄花翠竹都显得“清瘦”。这分明是她自身的写照——病痛使她形销骨立,但精神却愈发清峻。“清瘦”二字,既写物象,更写心境,展现了她即使在生命终点依然保持的审美自觉。这种将自我投射于外物的能力,正是诗人最可贵的品质。值得注意的是,她选择的是“黄花”和“翠竹”,这两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象征高洁的意象,暗示着她在生命终点依然保持着精神的纯洁与高贵。这种“清瘦”,不是贫瘠,而是去芜存菁后的精神提炼;不是虚弱,而是历经磨难后的风骨彰显。
“唯剩去年香,依然旖旎芳”,这两句将时间的维度引入词中,完成了从空间到时空的跨越。眼前的景物虽已凋零,但记忆中的芬芳却依然旖旎。这“去年的香”,是她对健康时光的追忆,是对美好往事的珍藏。在病痛折磨的当下,她还能从记忆中汲取芬芳,这份精神的富足令人动容。一个“唯”字,道尽了现实的残酷;一个“依然”,却彰显了精神的永恒。这两句词里,藏着她与丈夫相守的温馨时光,藏着女儿咿呀学语的甜蜜记忆,藏着在鸳鸯湖畔漫步的诗意时刻。所有这些美好的记忆,都化作了“去年香”,在她生命的寒冬里继续散发着温暖。这种将记忆诗化的能力,让她在现实的苦难中找到了精神的避难所。
下阕转入对生命的哲思。“人间难再少”,化用苏轼“人生难得再少年”的意境,却比原句更多了几分沉痛。苏轼是在感慨时光流逝,而她是在直面生命的终结。这句词里,有对逝去青春的追忆,更有对生命不可重复性的深刻认知。她或许想起了自己如花的少女时代,想起了新婚时的甜蜜时光,想起了健康时的自在岁月。所有这些,都如流水般一去不返。但这种认知并没有让她陷入绝望,反而让她更加珍惜当下,更加专注本质。这句词既是对逝去美好的哀悼,也是对生命有限的接纳。
“离别须臾到”,说得如此平静,却让人读之心惊。对于弥留之际的她而言,与这个世界的离别真的就是须臾之间的事了。这种对死亡的清醒认知,比死亡本身更让人心痛。值得注意的是,她用的是“须臾到”而不是“即将到”,强调的是死亡的突然性与不可预知性,这与她多年来的病痛体验密切相关。在病魔的折磨下,她早已参透生命的脆弱与无常。然而,面对即将到来的永别,她没有恐惧,没有怨天尤人,而是以一种异常平静的心态接受这个必然的结局。这种平静,不是麻木,而是经过痛苦挣扎后的释然;不是放弃,而是看清生命本质后的通达。
“仍执本心归”,这五个字,是全词的词眼,也是她一生的写照。在生命的最后时刻,她依然执着于自己的“本心”。什么是她的本心?纵观她的诗词创作,我们可以知道:是对丈夫始终不渝的深情,从《千秋岁》中的“妻孥住在天边月”到《瑞鹧鸪》中的“绣成新被两鸳鸯”,这份深情始终未改;是对女儿无法割舍的牵挂,从《容颜》中的“以为还是嫁君前”到《村居》中的“不是有人来”,这份母爱始终如一;是对诗词艺术至死不悔的热爱,从初学诗时的“程门立雪不甘休”到生命最后的创作,这份执着始终不变;是对这个世界始终如一的真诚,从《鸳鸯湖》中的“绿荷烟柳可相亲”到《算命》中的“最恼南村李半仙”,这份真诚始终未减。即便生命将尽,她依然要保持这颗赤子之心,清清白白地来,干干净净地走。
“不劳霜雪催”,结尾五字,说得云淡风轻,却蕴含着巨大的精神力量。霜雪,既是自然界的严寒,也是命运的摧残,更是死神的召唤。她说“不劳”,是一种何等的从容与淡定!这不是消极的放弃,而是经过痛苦挣扎后的释然,是看清生命本质后的通达。她不再与命运抗争,而是选择有尊严地接受。这种态度,与她早期在《咏梅》中“晓我当初何故栽”的质疑形成了鲜明对比,展现了她思想上的成熟与超越。此时的她,已经与命运达成了和解,与死亡达成了谅解。
“不劳霜雪摧”句,或许可以追溯到十天前的那场大雪。凤山是典型的南方,几十年都不见得下一片雪花,而就在她病情再度恶化的那几天,一场大雪意外而来。在她的想象中,这场雪是为她而来的,催促着她:“该走了……”。纵有千百般不舍,也得遵循命运的安排,只是,“你别催,我只想跟丈夫女儿道个别……”
这首词在艺术上达到了返璞归真的境界。与她早期作品相比,这里的语言更加朴素,意象更加纯粹,情感更加内敛。她不再需要借助繁复的修辞,也不再需要刻意追求格律的完美,而是用最本真的语言,表达最深刻的生命体验。这种艺术上的成熟,源于她对生命理解的深化。当一个人直面死亡时,所有的矫饰都显得多余,唯有真诚最为动人。
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词中展现的时间意识。从“去年香”到“须臾到”,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时间闭环。过去的美好记忆与当下的生命终点在词中交汇,让这首短短的小词承载了整个人生的重量。这种对时间的诗意处理,展现了她作为诗人的非凡功力。她将线性流逝的时间,转化为可以反复品味的诗意瞬间,让短暂的生命在艺术中获得永恒。
从文学传承的角度看,这首词既继承了古典诗词的优良传统,又赋予了它新的时代内涵。她将李商隐的深情、苏轼的旷达、李清照的婉约熔于一炉,却又注入了自己作为当代民间女子的独特体验。这种古今的融合,让她的词作具有了跨越时空的艺术魅力。更重要的是,她打破了传统闺怨词的局限,将个人的生命体验提升到普遍的人性高度,让她的词作不仅是一个女子的心声,更是所有面对生命困境者的共鸣。
与她其他晚期作品相比,这首绝笔词更多了几分哲思的深度。在《梅弄影》中,她还在为“怕损红颜”而忧虑;在《南乡子》中,尚存“留待千年后世尝”的期盼;而在这里,她已经完全超越了个人际遇,达到了对生命本质的洞见。这种思想上的飞跃,让她的绝笔词具有了非凡的哲学高度。
这首词的价值,不仅在于它的艺术成就,更在于它记录了一个普通人在面对死亡时的从容与优雅。在这个浮躁的时代,罗红端用她的绝笔词告诉我们:生命的价值不在于长度,而在于我们如何面对必然的终结;诗歌的真谛不在于技巧,而在于是否用最真诚的生命去书写。她的词作之所以动人,不仅因为其艺术价值,更因为其中蕴含的生命态度——即使在最困顿的处境中,也要保持精神的尊严;即使在生命的终点,也要唱出最美的歌谣。
今天,当我们重读这首绝笔词,秋风依旧年年吹过,黄花翠竹依旧岁岁枯荣。罗红端已如她词中的秋草,归于尘土。但她用生命书写的这些词句,却穿越时空,依然在我们心中激起回响。这首词让我们明白:最深的痛苦,可能开出最美的艺术之花;最短暂的生命,也可能留下最永恒的印记。
在这首绝笔词中,我们看到了罗红端作为民间词人的独特价值。她用最传统的文学形式,记录最真实的生命体验;用最典雅的诗词语言,诉说最质朴的人生感悟。这种将生活升华为艺术的能力,让她的词作超越了个人悲欢,成为一个时代的诗意见证。她的创作,填补了民间诗词的一个重要空白——让我们看到了在主流文学之外,那些用生命写作的普通人如何用最真诚的方式,记录最真实的人生。
当我们细细品味“凋零透”的彻骨寒意,“清瘦”的风骨,“去年香”的温馨,“本心归”的执着,“不劳催”的洒脱,我们仿佛能看见那个广西山村的女子,如何用她柔弱的身躯承载起生命的重量,如何用她敏感的心灵完成最后的歌唱。在这个意义上,罗红端和她的绝笔《菩萨蛮》,已经不仅是一首词、一个词人,而是成为了中国民间文学中一道独特的风景,永远摇曳在时光的深处。
她的绝笔词提醒着我们:在物质匮乏的处境中,依然可以保持精神的富足;在命运的重压下,依然可以活出尊严的高度;在生命的终点,依然可以唱出最美的歌谣。这,或许就是她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启示,也是她所有诗词创作最核心的价值所在。通过这首绝笔词,罗红端完成了一个普通人不普通的生命叙事,她用三十三年的短暂人生,书写了一部关于爱、关于美、关于尊严的生命史诗。
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,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,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,请点击举报。配资炒股网官网,炒股配资股票,长沙股票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